六安有座“英雄山”
——皖西籍著名作家徐贵祥《英雄山》新作访谈
编者按:参军之前,徐贵祥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个英雄。
他曾亲历两次战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历经严峻的生死考验。他也用自己的笔在一部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塑造着令人心生敬意的英雄人物。新书《英雄山》同样书写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近日,本报记者连线皖西籍著名军旅作家徐贵祥,访谈现作整理,今日刊出,以飨读者!

记者:首先祝贺徐老师,继2019年《中国作家》推出您的长篇小说《穿插》之后,英雄山系列《穿插》《伏击》近日又隆重出版发行,读者反响热烈,家乡读者尤甚,徐老师能介绍一下吗?
徐贵祥:英雄山系列《穿插》《伏击》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记忆深刻,我们有很多文学作品都在表现,但是,我觉得还是冰山一角,这场战争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值得挖掘,比如人性,比如民族精神。我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都是常规战争,使用的都是一些轻武器,枪和炮,甚至更原始的武器,像大刀之类的,这样的战争在进行时是非常残酷、惨烈的,因为这种轻武器它可以短兵相接,视觉上更具冲击力。
因为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带着浓郁的大别山色彩,有很多故乡元素,所以家乡读者更多关注一些。这次的《英雄山》依然以我所熟悉的江淮文化为背景底色,出版后,我自掏腰包购买了一百多套,分别赠送给家乡的亲友们,感谢他们对我文学创作一如既往的关注。如今生活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我不指望收到书的每一个人都能认真阅读,寄出的这百余套书,如果有十套被人认真读过,并能唤起几个人对家乡红色文化、江淮文化以及军事文学的兴趣,哪怕有三个人,甚至是一个人,因此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徐老师的作品其故事大多发生在皖西抗日敌后根据地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小说中的战争英雄们有八路军将领,也有国民党友军,还有当地的游击队员,进步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各显其能,充满了人生智慧和战争智慧。去年我在《中篇小说选刊》5月号上读过您的中篇小说《鲜花岭上鲜花开》,同期还有您的一篇创作谈《擦亮我们的英雄,才能照亮我们的未来》,观点我很认同。这一次读《英雄山》,感觉更不一样,读着读着,内心就升腾起一股豪气,这股豪气与一方水土有关,六安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个生命都有一段潜能无限的英雄之旅。
徐贵祥: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西南方的大山里有红军,有很多英雄。当时,还有很多民间文学,比如大鼓书,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乡村文艺节目,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从此之后,关于革命、关于平等、关于理想、关于信仰的各种想象就像种子一样埋进我的心里。
谢有顺说散文写作要有精神根据地,小说创作也是同理。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经验,感受,欢乐,悲伤,都是来源于此。写作上的“回家”,重要的在于如何找到可靠的载体,把“一个地方的灵魂”乃至“一个民族的灵魂”诠释、透显出来,譬如说,英雄大别山,以及英勇的大别山人民。我们不仅仅要仰望载入史册的英雄,还必须敬重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军事文学的创作者,寻找英雄、发现英雄、捍卫英雄,我责无旁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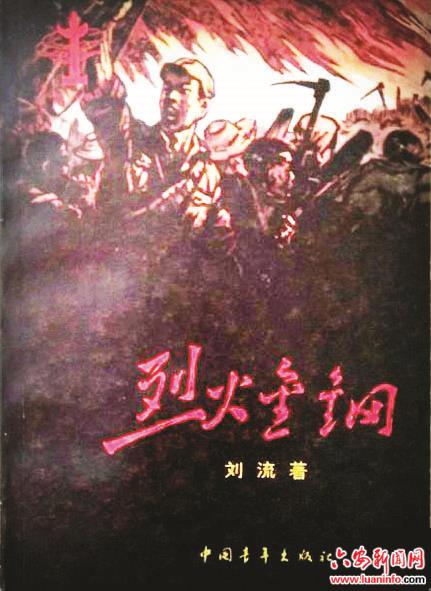

记者:徐老师之所以能刻划出一系列鲜活的英雄形象,并且展示出他们智勇双全的英雄气概,这可能与您从小就崇拜英雄,想当英雄的理想有关。那么,您还记得读过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吗?您认为一篇作品打动您的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是英雄精神吗?
徐贵祥:我可以讲讲童年阅读印象最深的作品,连环画当中记忆最深刻的是《草上飞》,小说当中印象最深的《烈火金钢》。多年后总结,我对《烈火金钢》之所以有兴趣,除了英雄人物史更新和丁尚武、肖飞等人个性鲜明、战斗勇敢、事迹传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物关系复杂,特别是何大拿一家,何大拿本人是汉奸维持会长,大儿子何志文是鬼子翻译官,二儿子何志武是国民党特务,而何大拿的女儿林丽,则是八路军的女医生。这个家庭成员的组合不仅让年幼的我产生很多遐想,即使几十年后,当我已经成为一个主攻战争文学的作家之后,我仍然认为,作者这样设计人物关系,令人深思,耐人寻味。这个家庭,甚至可以看成是抗战初期底层人民精神和行为的缩影,尽管它仍然带着阶级划分的特色。
一个英雄的成长,有很多因素,文化心理结构非常重要,也就是要有英雄意识。其次就要看机遇了,看战场环境,看个人遭遇。我对自己有个认识,我觉得,给我机会,我当英雄的概率远远大于当逃兵的概率,机会合适了,我当英雄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我是有英雄梦想的,也是有爱国精神的,更有“马革裹尸”的思想准备。参战那会儿我给家里写信,把我的亲人吓得不轻,里面豪言壮语很多,确实挺吓人的。我一到战场就立了个三等功,是全团新兵当中第一个立功的。第一次战斗之后,指导员把手枪交给我保管,他自己扛上了冲锋枪。那几天我背着指导员的手枪,感觉非常神气,如果正好那几天同敌人短兵相接,我一定会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一样冲锋陷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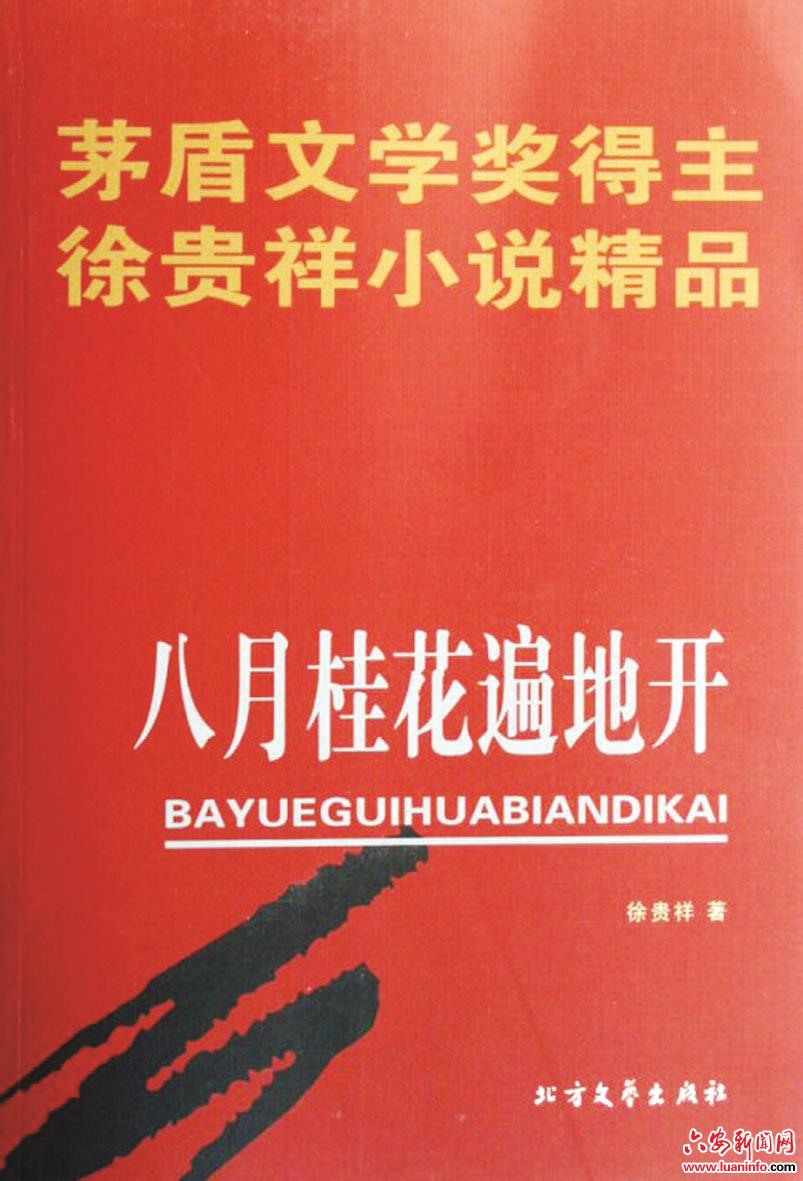
记者:六安红色文化就好像漫山遍野的杜鹃,静止是美丽的,但有风轻拂,这份美丽就更具生机与活力,《历史的天空》是风,《马上天下》是风,《八月桂花遍地开》是风,《鲜花岭上鲜花开》是风,《英雄山》也是风…… 它们吹得漫山花枝乱颤,那些曾经的英勇过往才得以一一呈现。
故乡之于您,可以说是一处不断从中汲取营养和精神力量的土壤吧?
徐贵祥:叶集西接大别山脉,南依淮河水系,史河干渠穿镇而过,接壤两省三县,是鄂豫皖三省的结合部,曾有“鸡鸣三省”之说。同时,这里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著名的将军县金寨和叶集同饮一河水。我早年读过的小说《破晓记》,把叶集描述得像一个神秘的城市,有着很多神奇的人物和故事。尽管我后来参军,当了作家,有了各种身份和头衔,但我的身上永远摆脱不了故乡的泥土气息。我的故乡诞生过那么多杰出的人物,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小时候耳濡目染,长大了浮想联翩,它们积淀在我的血液里,活跃在我的血管里,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我一直保存着两本《皖西革命史》,家里和办公室各有一册,什么时候想看,顺手就找到了。记得有一次,在东河口镇老基层干部陈良亭的家里,我看到了民间缴获的几件日军作战用品和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成为一个线索,引导我继续探究家乡的抗战故事。还有一次休假,史红雨老师带着我遍走皖西山水,一路上给我讲大别山的故事。有一次他指着几个正在村头闲聊的老汉对我说,这些人里面可能就有老红军,当年参加革命,甚至成为连长、团长、师长,以后因种种原因隐姓埋名的大有人在。史老师的话让我震惊,让我对家乡的每一个老人都刮目相看。战争结束后,那些参加过战斗的人物在哪里?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常常在想。

记者:您渗透于全部作品中的英雄精神和英雄情怀,总能让读者血脉偾张。那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立体饱满,叙事很有画面感,尤其是战争场面,读之,身临其境。
徐贵祥:过去在读军校时学炮兵参谋业务,我有两个方面学得好。一是军事地形学,那时候我们站在山区的某一个高地,看到山川河流道路,我脑子里可以马上形成一个画面,可以精确目测它们之间的方位关系和距离。二是地形图,地形图上有等高线,等高线越密集说明越陡。有了等高线,地图在我面前是立体的,可以变成沙盘。在侦察地形时,我可以利用瞳仁之间的距离形成弧形的弹道——我是带着艺术欣赏的心情学地形学。所以我写战术性极强的战争时有画面感。这是行业文化,是职业知识带来的技术创作。从技术、战术到艺术,这是一个军人在战争当中汲取的营养,同时也给创作带来精神的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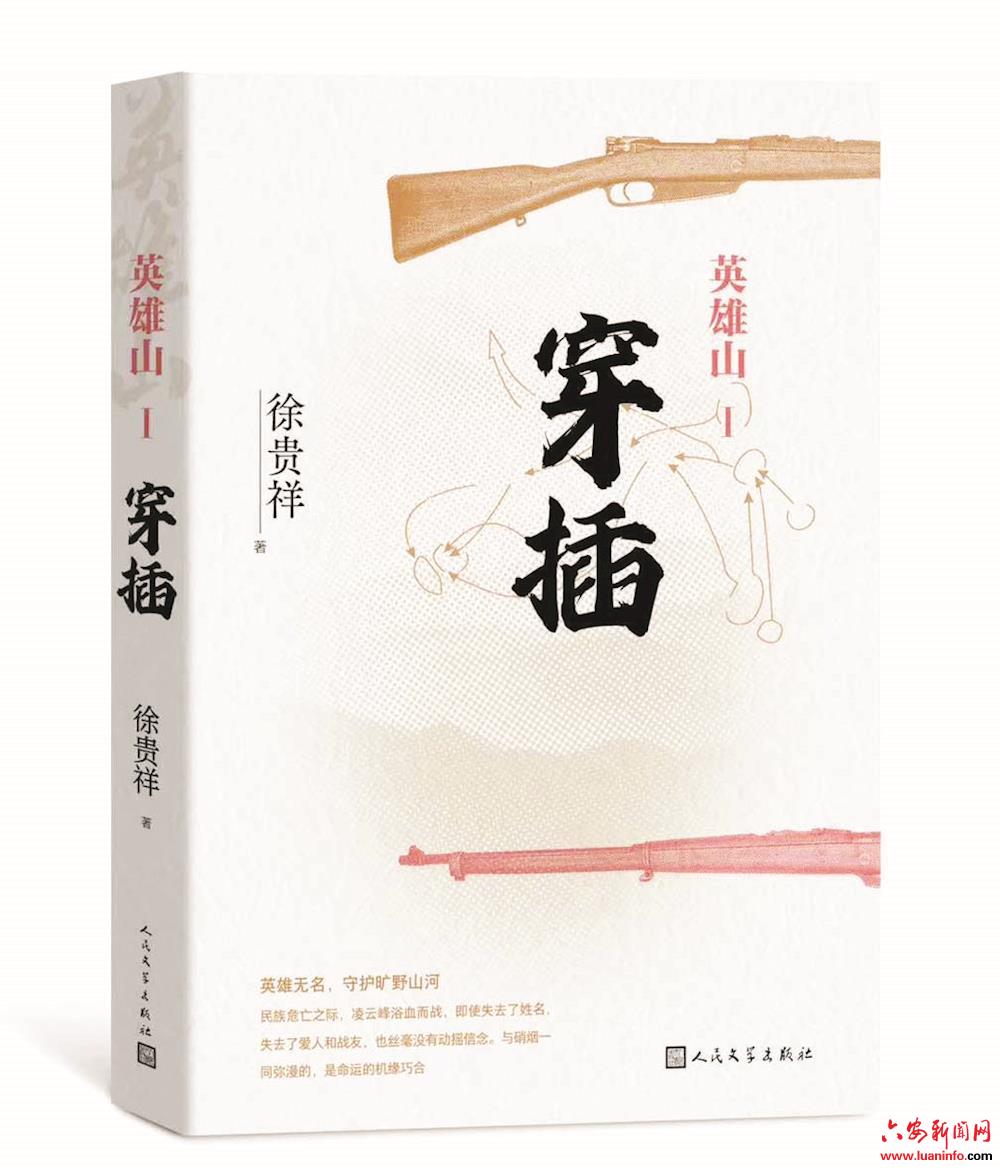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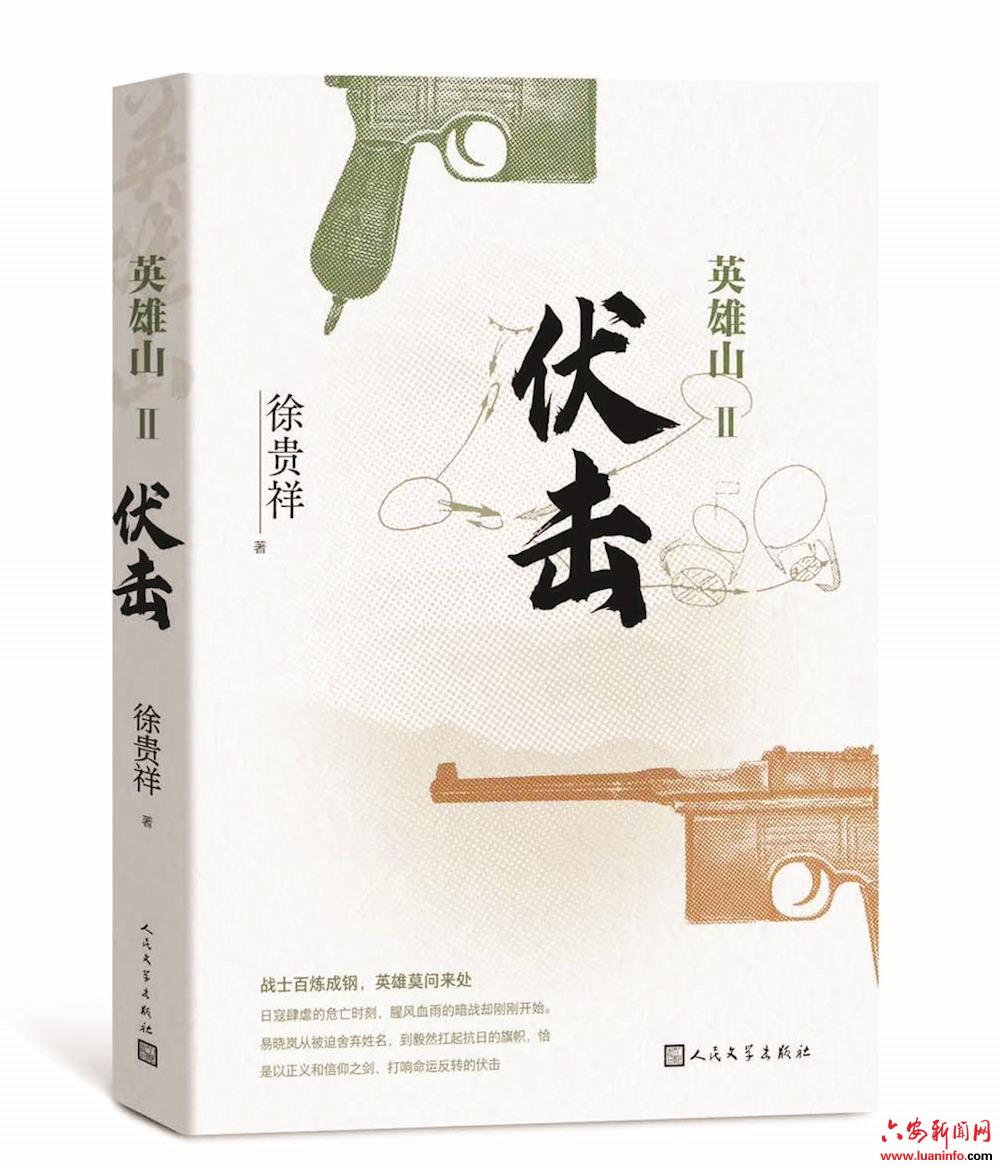

记者:有评论说,徐老师是“正面强攻军事文学”的作家,不仅不落前人窠臼,也很少重复自己,每一部都有新意,思想高度是递增的,艺术水准是上升的,叙事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家乡文友很想听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经验。
徐贵祥:谈不上经验,谈谈真实的体验吧。
“不落前人窠臼,避免重复自己”,这话说起来容易,进入操作层面,可能千难万难。我的作品,要说完全没有重复,那不可能。但我心里有创新意识,有对重复的警惕,重复得少一些,新东西多一些,这是我力所能及的。
除了写作训练,我还有两笔财富。首先,我同样是个阅读着,特别是战争文学作品,读得越多,遗憾越多。每次阅读,就有很多想象,老是想对别人的作品进行补写、续写、改写、甚至重写,在这个过程中,脑子里库存了大量的想象。其次,我还是个战争亲历者,而且是两次,特别是第二次,血气方刚,踌躇满志,一年内由小排长升到正连级,这一年的战争体验,是我创作的巨大财富,在以后的创作中,每当设计一场战斗,我的脑海里就有鲜活的形象,山川、河流、丛林、道路、高地……当然还有军人的心跳。当你在丛林里潜伏八天八夜,当你从雨林里接过战友的担架,当你从一场战斗中死里逃生,当你从猫耳洞里睁开眼睛,你看到的月亮都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你可以把月亮写得像万花筒一样斑斓,可以写出一千个绝不重复的月亮,到底写成什么样子,要看写作时心里的底色。阅读积累、亲身经历、如梦似幻般的回忆和思考,构成了我的材料库存,一旦我找到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进入写作状态,那就非常流畅,就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淌。从自己的血管里流出来的东西,很少同别人重复。

记者:在《英雄山》的创作中,您的英雄情结一以贯之,但我发现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叙事角度变了,“灵异”视角从一开头即在读者眼前升起了一个悬念,引人入胜。接下来,环环相扣,动人心弦。
徐贵祥:多视角进入写作,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谓的现代性,首先是视角的现代性,然后才是视线、视野的现代性。创作《英雄山》,我确实尝到了“灵异”视角的甜头,其实这个视角同“全能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被用多了,用滥了,用得让人心生疑窦了,变成陈词滥调了。我这里换了个视角,其实也是雕虫小技。这两部作品,形式上的探索有很多,有的是主动的、设计的,而更多的是被动的、始料不及的,是写作过程中老天爷空降下来的,属于神来之笔。我本人说不清楚有多少技巧、有多少创新,这个恐怕读者比我更清楚。
记者:说到叙事,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您把这两部作品分别命名为《穿插》和《伏击》,是不是想特别突出军事文化元素?
徐贵祥:《穿插》和《伏击》这两个书名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具体的战例和战术,事实上,这两个属于军语的动词,在作品里只是一种隐喻,是那些匍匐在生死线上具体的人的情感的穿插和思想的伏击,我的创作主旨,是从根本上表现觉醒的良知、激活的感情、爆发的动力、高举的信仰和升华的境界。当然,我是军人,而且两次参战。当基层指挥员的时候,学过战术,学过地形。后来当编辑,研究过战史和战例,军事常识比较丰富。我写到战争和具体的战斗,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写出来后就有画面,有动感,挥洒自如,有视觉冲击力。
记者:两部作品整合为“英雄山系列”,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可能有第三部、第四部?如果有,是否依然有家乡的元素?
徐贵祥:完全有可能,至少第三部已经在心里播下了种子,只要有精力,我就会把它写出来。但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发酵期。这第三部,我既不能重复我过去的作品,也不能让它成为《穿插》和《伏击》的延续和补充,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层面,必须有新的东西。
关于家乡元素,可以这么说吧,她在我所有的文学创作中是无处不在的。鄂豫皖、大别山,还有我们皖西,是座宝库,英雄的故事取之不竭。
记者:《穿插》和《伏击》同时推出,引起很大关注。这两部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是各自独立的?
徐贵祥:说到这两部作品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做“藕断丝连”,这样说就比较清晰了,“藕”已经成了两截,但是还有“丝”相连,若即若离,可近可远。从时间概念上讲,故事大致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但是空间不一样,彼此的关联主要是因果关系,很少犬牙交错,因此它们各自具有独立性。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记者:从您的创作谈里我们知道,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历史资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的短暂行踪,最后演变成两个人、一群人、数十年、方圆千里的战争。人物之多、事件之多、矛盾之多、反转之多,都是您以前的作品所没有的。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并没有感觉混乱,而感觉到逻辑清晰,不断地满足阅读期待。这应该得益于结构的精心设计。
徐贵祥:小说当然要讲究结构,结构的基本元素是人物关系、故事逻辑、时空置换、情节调度、语言张弛等等。这两部作品,结构有个大方向,就是人的命运,分别以红军军官凌云峰和原国民党军官易晓岚为核心,以他们的命运走向为基本路线,相向而行,擦肩而过,角色转换,殊途同归,向死而生,死而后生,这种结构是隐形的,遵循的是“目标牵引”的法则。这里讲的是大的结构原则。
记者:您的作品始终高扬英雄主义的旗帜,洋溢着阳刚之气,这是读者的强烈感觉。但在《英雄山》两部作品里,似乎有些变化,刚则刚硬,柔则柔情似水。关于爱情的描写,也大气磅礴,回肠荡气。何子非与张达理、凌云峰和安屏、楚大楚和蓝旗……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又干干净净。
徐贵祥:写这两部作品,我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何子非这个人物有原型,是国民党部队里俘虏过来的军官,有点骄奢好色,爱吃辣子鸡丁。我写爱情写得不多,可能体验比较少。但是张婆娘这个人物写得比较满意,写出了中国农村妇女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性格。起初“张婆娘”听说何子非是国民党军官,端起剩菜就要摔到何子非头上;当何子非造了桥,她又杀鸡犒劳何子非。张婆娘后来参军改名为张达理,何子非在长征路上奄奄一息,是张达理背着他渡过生死关。当他死里逃生睁开眼睛,看到阳光从外面射进来,落到张达理的脸上,让他想到了圣母——人的感情是随着时代、随着经历发生变化的。
创作这两部作品,我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就是从残酷中捕捉诗意。主人公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爱情很难描写。那个年代,那种环境,缺乏表达爱情的契机,要有交集,有冲突,才有可能“死缠烂打”,才有可能使感情升级。凌云峰和安屏之间很难有更多的交集,所以我设计了桃木匣子和柞绸马甲,通过这些物件传达他们的感情交流。抗战池为什么出现?我要让楚大楚带着部队去洗澡,要让楚大楚和蓝旗在生死决别之前的爱情和性爱非常高尚、圣洁、庄严。在一个必须的、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时候,不得不走到一起的地方,在那个午后,完成值得永久回味的、具有庄严仪式感的一次美丽的行动。我不回避美好的爱情甚至性爱,但我不敢轻易下手,怕玷污了神圣的美好。对于我来说,是郑重其事地、虔诚地写人性的美好。我为此准备了几十年。
记者:耽误您这么长时间,谢谢徐老师,欢迎经常回来!
徐贵祥:会的,因为我的家在六安。
(皖西日报融媒体记者 流冰 )






